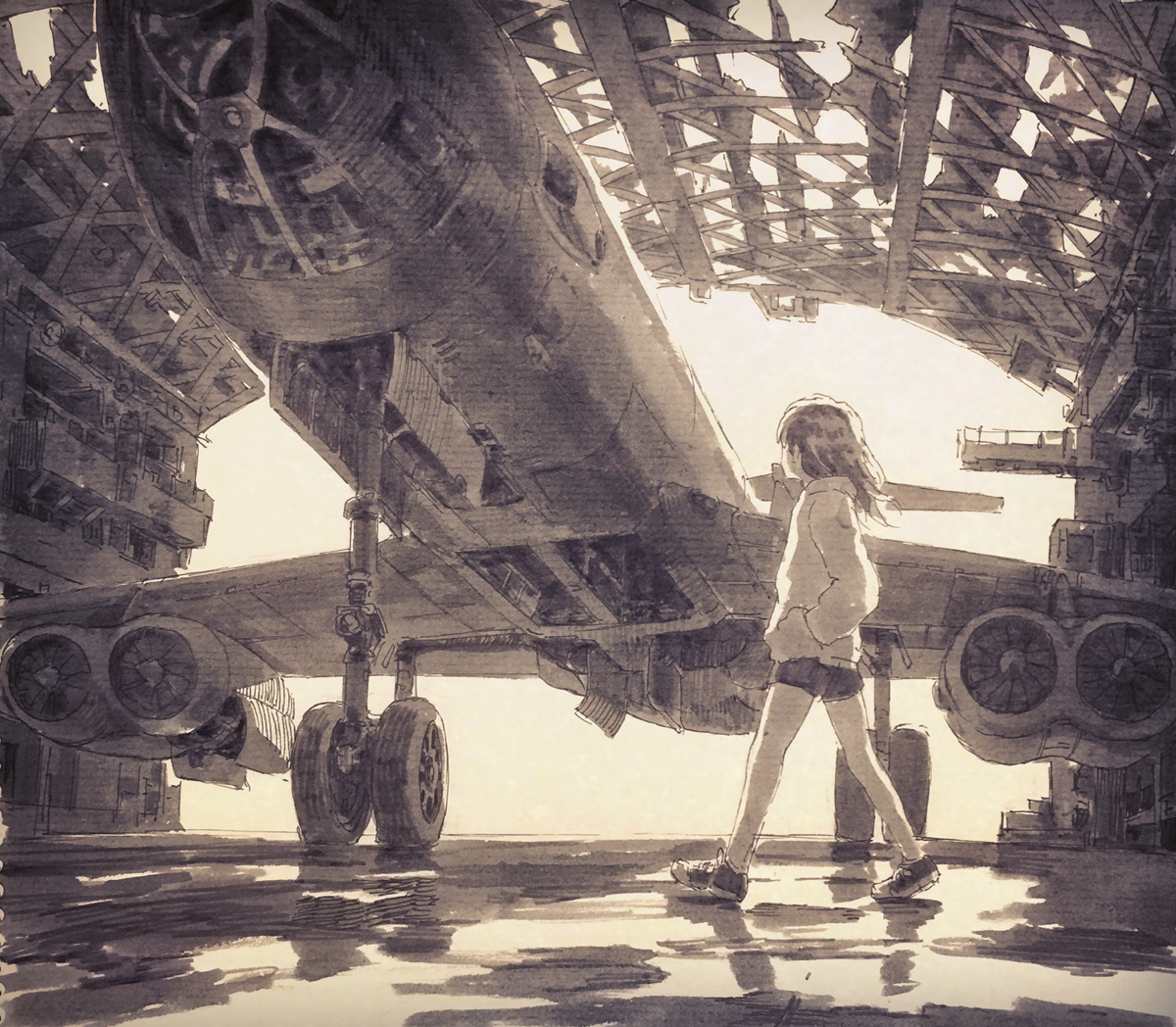鉴证的逻辑(1)——极权国家、全民党与乌云
"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序
鉴证是什么?如果你水平很高,你会从抽象、具象,从意识形态,社会科学角度侃侃而谈政治。如果你岁月静好,你会在某个政治立场测试的“不关心政治是正确的行为”选项下选择非常同意。如果你喜欢迪士尼,你会对动画中可爱的熊科角色品头论足。而在现实中,鉴证一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饭后娱乐项目,进入信息化时代中这种活动正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世界互联网大厕所的各处。在这个古老的国家,从正在南美雨林中走线的无国界人士到人人都喜欢的前复旦大学社科偶像,似乎无人能与政治脱离关系。政治是那样的广阔,所有的课题都可被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而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然而鉴证和治国理政的差异在哪?鉴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谁让我的强击池沉船了?在诸多问题的困扰下,我便立志要抽丝剥茧般理清鉴证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经济活动从处在社会秩序下的人类活动中诞生,所以“任何政治学说的逻辑和现实起点都是人本身”,现代国家都是民族国家,都会念经的你肯定知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所以观察鉴证逻辑,我们先要假设存在一个平行的世界,在这个与OTL似乎没有差异的世界中,存在着一个叫做契丹的完全虚构国家,文中所描述的任何情况事件都发生在虚构国家契丹中,本文不存在任何观点,不输出任何思想,所有文字都由AI生成,不代表博客网站任何立场。
极权国家与先锋队
在国际学术上,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对于政治的研究是十分模糊的。现实的人的是构成政治社会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将与社会和自然紧密联系的人定义为“现实的人”,这是马克思学说对费尔巴哈“自然人”学说的继承和批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人的定义更像是自然人缠绕上自然人在阶级社会中附带的社会关系。既然人构成了政治的前提,我们便能欣然接受各种不同的政治学说,正所谓什么树结什么果,人对政治不同的看法源于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此的解剖,我们便能回答第一个问题,契丹是不是极权国家。
当然不同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而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看待极权国家这个标签。你很厌恶契丹,恨不得颅内脱离这个邪恶帝国的国籍,但同时你又熟悉任何关于目田的理论,经常感叹“真伟大啊,哈耶克”,你会回答是的,现在的契丹是极权国家。你很有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应该以本民族的出生为荣,同时你又每天批判协商民主,满口“先锋队、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阶级专政”,但你也会回答是的,现在的契丹是极权国家。从这两种魔怔鉴证人的相同表现中我们能学会什么?答案,目田和左∠都是低能。哦,当然不是,我们能得知这两类人身处完全相反的政治立场却得出相同答案的原因是,他们对极权国家看法的差异。第一种人有逆向民族主义倾向,厌恶契丹,同时又信奉西方民主,他们痛恨任何政府对自己的控制,认为“极权国家”是法西斯式恐怖统治的代名词,理所应当地贴上了标签。第二种人喜欢契丹,他们也觉得“极权国家”是“罗伯斯庇尔专政式”的统治形式,一段时间内的革命先锋队专政是实现恭馋主义社会必须经历的,我去,这简直太革命了,真是公公又铲铲牙。追溯历史,“极权国家”或者说是“全能国家”的来源,就是形容纳粹,这是一个从诞生起就沾满了意识形态的词汇,当然苏东体系和苏马理论崩溃和解体后,这些词越来越多地成为了西方意识形态下的贬义词,用来攻讦与他们体制和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
但如果研究这些类似的强权国家你又会惊讶的发现,就算不是极权国家,他们中大部分走向腾飞的过程又是不得不依靠一个强力政府。那些没有赶得上两次工业革命的,被历史车轮无情碾过的可怜虫,最后却又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之中。史达林的快速工业化,齐奥塞斯库的黄金时代,朴正熙的汉江奇迹,你可以说在这些“独裁者”之前他们的国家已经完成了可观的工业积累,但是量变能否到达质变并不是一定的,可能缺少了这些人的作用,那量变只会一直积累下去。科学告诉我们不能迷信经验,但这些海量个例又强而有力地印证了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政治历史的认识论,还是十分受用的。考茨基的议会斗争与列宁的武装斗争的区别是,后者成功了。历史的车轮不断鞭挞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而这些“强权国家”的政府裹挟着他们的国民,不断地前进,没有人知道这场旅行的终点,没有政府能向他们的国民承诺所有的期望都能够实现,而若干年后他们中的一些在自己的矛盾之中崩溃了,一些最终停滞了下来被卷入历史的尘埃,还有一些仍进行着这一场苦难的行军。停下一节老旧的机车只需要一步,拉动制动阀。但车上没有人知道这架机车是否会因为巨大的惯性而解体,是否会因为崩断制动而跌入永劫不复的深渊。
如果抛开偏见,但就考虑它们本来的定义,政府的影响力在国家中的作用。契丹是完全的先锋队国家,CPC又是完全的列宁式政党,有形的大手把控了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各种事实都在印证契丹就是极权国家,但这进一步让人疑惑,先锋队和极权国家的区别在哪。作为康米党所有实践中唯一成功的尝试,弗拉基米尔的先锋队理论意图构建一个完全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架构,通过对孟什维克事件的反思,弗拉基米尔进一步加强了一党专政,阶级组成政党,政党代表阶级同时完全控制了国家。任何政治思想的实践的前提都是夺取政权,卢森堡在德国革命实践的失败,从侧面证明了民主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政权建设中的问题,这迫使弗拉基米尔愈加小心地处理民主问题。先锋队国家中大部分的民主决策只存在于先锋队内部,民主过程却在社会中广泛存在,无论是契丹的民主生活会,素黏的苏维埃民主。世界上仍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包括契丹基本都是先锋队式的,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古巴是一种另类的先锋队,卡斯特罗认为先锋队的作用应该更多在教导人民,所以你会发现在古巴党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随处可见。先锋队通过控制暴力机器控制了政府,政府又指导着国家的前进方向。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些国家的权力结构,赫鲁晓夫战胜马林科夫的政治斗争,在本质是党的第一书记战胜部长会议主席,党战胜了政府。
弗拉基米尔的先锋队非常像是一种另类的“极权国家”,政府影响力巨大的本质是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需要。但先锋队的腐化又是需要令人警惕的。卢森堡担心先锋队的腐化,列宁说到先革了再说,这时候凯恩斯却跳出来大叫“长久以来,我们都死了”。极权国家的辩论仍将继续下去,这是没有终点的,因为研究政治的学说就是研究人的学说。
全民政治
全民党最开始是社会民主党提出,康米党往往用此来攻击社民党右倾的改良主义,也就是“修了”。但康米党在自己之后的实践中却普遍转向了另一种性质的“全民党”,这不可谓两个难兄难弟的殊途同归。按照康米们的理论,先锋队的建设必须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阶级性,在素黏,这导致了1933年联共党员只有190万,只有全国人口的百分之0.011。你可能会惊讶这看起来不挺多的,但先锋队国家是一党专政的,这意味着一个190万的联共组成的“全能政府”需要统治一个人口接近两亿的国家。如此来看,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岌岌可危的,甚至还要组建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拜占庭式”的官僚机构,190万人只是毛毛雨一般。同时严苛的标准会危害党的流动性,看似困难的门槛反而加速了先锋队的腐化。党缺少了新鲜血液的流入,失去了新陈代谢的能力。
解决先锋队国家的上述问题,最蠢的方法就是学习社民党的“全民党”理论,但这却又是看起来最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中也都被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史达林用大清洗保证党的纯洁性,也用人用自己的威望发动一场全民的政治运动。这两个例子的发生都有其他特定的历史原因,但客观上来说都防止了先锋队的腐化,但他们的继承人却又都大声宣告“党已经消灭了阶级,现在党已经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党”。看起来经过他们前辈的社会主义建设,阶级已经消失了,革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事物总是螺旋上升,这伴随人类文明诞生的东西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被消灭。
用全民政治的理论,既巩固了先锋队的政权,又使原来固化的干部阶层看似流动了起来。但路越走越偏,很可能的是一个不小心翻进了阴沟。一个长时间维持强权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权的强正统性。所谓“政治正当性来自被管治者的同意”,革命产生的政权正统性最高最正义,政变产生的政权正统性最低最脆弱。一个原先阶级性强烈的政党若是突然转向全民的路线,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很大地依靠自身的合法性。然而政权的正统性不会一成不变,这依赖于社会稳定与国民生活的质量,正统性降低,全民党政权就会变得摇摇欲坠。同时“阶级”可谓康米党的灵魂,丢下了灵魂的康米党不得不靠着大量的宣传与政治工作维持自己的存在意义,用来显示自己与“修了”的社民党的不同。若是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动荡,政治松动。那么恭喜你,这样的先锋队离自我崩溃已经不远了。
我们不知道从阶级政党转向全民政党是好是坏,没有人建设成功共产主义社会,但时间会给出答案。从80年代的“解放思想”到90年代“允许企业家入党”,契丹全面地转向了全民政治,政治的巨大地震在底层的反映就是社会的不稳定,但时间总会抚平社会的伤痕,经济的快速发展会掩盖那些问题,几十年后的人们仍旧会怀念那些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时代。
乌云···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三次分裂,第二国际的分裂诞生了社民党与共产党,社民党逐渐右倾并抛弃了马克思;共产党的分裂造就西马与东马两个马克思学派,西马由于太久地脱离执政党,政治理论已经偏离了现实;东方马克思学派的分裂使契丹与素黏两党走向了对立,素黏最终解体,国际共运陷入最低潮。亚伯拉罕第四教重复上演着派系间的分裂与对释经权的争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上空笼罩着许多乌云,但最大的那朵一定是史达林。史达林与契丹又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契丹是一个改得史达林都不认识的史达林模式国家。史达林模式下的国家一般有五大特征:快速工业化、高压的政治环境、政府指令型计划经济、全能型政府和特殊的民族政策。作为契丹甚至是后来几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学习素黏的路线基本上是唯一的选择。但不用细看都知道,这一套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套用的范围有限,而且还有很多要命的问题。可以说最适合史达林模式是那些工业落后,矛盾尖锐,政党合法性高的多民族国家,例如史达林模式的实践就在捷克斯洛伐克遇到了水土不服。当然即使是适应实行这一模式的国家最后也不得不转向对史达林模式的改革,即使是猛烈抨击史达林的赫鲁晓夫也不得不继续沿着这一条路线摸索。
当然,有果必有因,史达林模式是当时种种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快速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高压的环境应对的是当时糟糕的国际环境——如马克思预言那般蜂起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到来,素黏可谓孤立无援。善于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备的品质,但让一艘巨轮改变航向是非常困难又需要巨大代价的。现实中的政治,每个人不是只会接受指令的机器人,基层政府也不是中央的复制人,你振臂一呼,不是所有人都会听你号召揭竿而起。史达林就这样像一片乌云笼罩在了后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党的头上,这一片乌云久久无法散去,史达林的诅咒仍会跟随他们相当长的时间。
你也许只能从如今契丹的民族政策中看出史达林的影子,史达林从社会主义角度阐述的现代民族理论是十分成功,你能从今天契丹的相关政策中看出这一理论的最终形态。现代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解构了民族如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失去存在的根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无法跨越这一巨大鸿沟。
鉴证的意义
鉴证的意义在于,鉴证没有任何意义。现实的人是经验的人,这比较复杂,第一层含义是作为人是由于上述特征的存在而成为现实的经验过程;第二层是经验过程可以经验确定,而不是依靠臆想和猜测。鉴证脱离了对现实的考察,只依附于对自我经验的叙述。所以鉴证其实只是一个论点输出的过程,你输出你的看法,然后给所有与你意见相反的人贴上种种标签。但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他自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鉴证其实也是一个人实践自己世界观的过程。
末
喜欢宏大叙事,是有对自己成为这一个巨大集体的一员而感到喜悦。他们坚信着人民史观,对个人在集体中而推动历史发展继而觉得欢欣鼓舞,于是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厌恶宏大叙事,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对使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毫无帮助,比起宏观的事物,他们可能更想过人生赢家的生活,什么狗屁主义的争论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事实上更多人只是在自己或平淡或苦难的生活中随波逐流,比起治国理政,可能收到200块钱更能取悦他们。正所谓“为了一块牛排出卖巴黎”,当生命的存续成了问题,还有多少人记得什么公义主义。当然,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当政治从高高在上的神殿中跌落,鉴证变成了碌碌众生一项寡淡的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