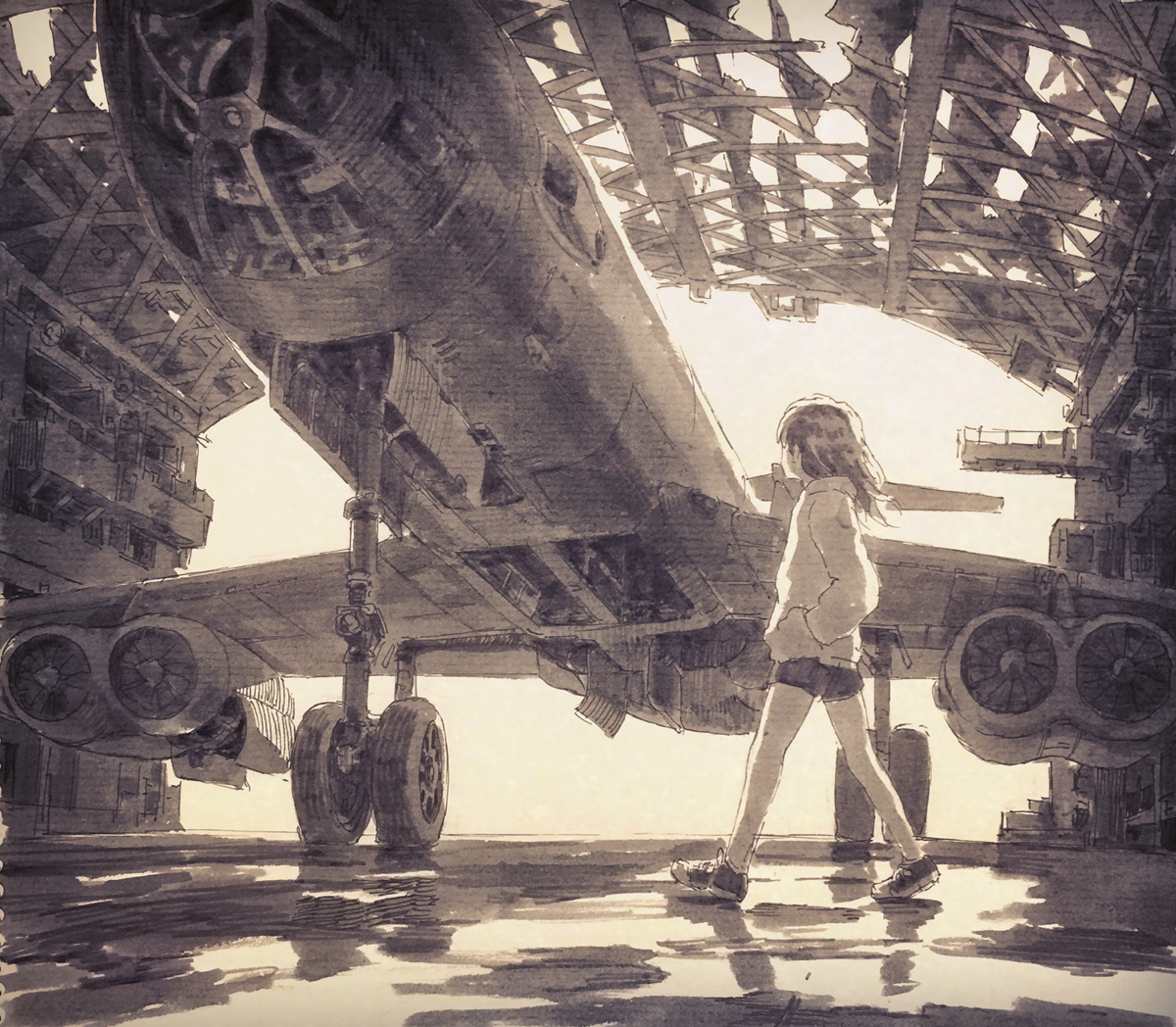献给努力家的赞歌
"来吧,一同跨越所有血统与阶级吧"
献给努力家的赞歌
————致小栗帽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成年的我现在暂且回答不上来,我自认为自己现在是已经退化成猫奴了。但如果你有时光机,回到过去去询问小时候的我,那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我最喜欢的动物便是那些驰野在草原上的骏马。
父亲曾在青海当区队长,青海和西北那一带是我国的著名马场了,特别是以出产优质军马而出名。听父亲说在那个时代的青海,一个会骑马的小伙子相亲时甚至能胜出城里的科员几分,大抵是同蒙古同胞一样的道理吧。可我的父亲,一个山东父亲与贵州母亲生下的,从小生长在江南小城的人,竟能津津有味地与我说上一天他在青海与那些威武马儿的故事,从跨马的方法,怎么踩马镫到他自己与别人在马场赛马的轶事。已入中年的父亲老早就养起了啤酒肚,可在话语间却仍透露着一丝轻狂少年的傲气。大抵是那时候,尚年幼的我心里就有了一副戎装少年骑着棕红枣马驰骋在地平线上的画面了。
除去父亲的天天吹牛,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真的马大概是幼儿园在公园门口看外地来的杂技团表演时了,纵使小时候的记忆有许多都早已忘掉,但多年之后我仍能记起杂技团里那匹瘦骨嶙峋得叫人分辨不了到底是骡子是马的动物。可能当时在一个小朋友纯真的心里,这与他所理想中的骏马差了千里了吧。见到我朴素幻想中的马,那还是在零九年左右,同父亲回青海看望朋友,看见了幻想里的骏马,油光发亮的枣红的毛与健硕的肌肉,它的每一次迈步都仿佛在诠释何为有力二字。甚至于连父亲也感叹道,像这样优质的马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了。可是我却总感觉那马还是与我真正理想中的模样差了点样子,多年后的现在再回忆起当时,也许是那枣马的眼神罢,那是慵懒的,无精打采的,人性与野性全部消失殆尽的。总之说白一点,那就是混吃等死的模样。想想也是,作为训练出来招揽游客的马,早早地失去了野马的野性,赛马的高傲,军马的肃杀,只是空有副好身子罢了。不用努力,从出生起就是玩赏物,空洞地等待着老去,这不是我心中的骏马所该有的。
我最喜欢的马是小栗帽。那大概是一零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与小栗帽相遇是中央四套的世界名马一览上,那时候央视总是喜欢整一些新奇玩意,即使是在国内不温不火的赛马。其实在我第一次从电视里看见小栗帽时,她已离开世间,据我的记忆,那大抵也是一零年吧。可这并不妨碍幼稚的我被那满身灰色的扎眼的赛马所抓住眼球,与我想象里要不棕红要不雪白的马的样子完全相反,那是颜色可是纯纯的深灰,如乞丐的补丁一般,但又如同是瘟疫骑士的坐骑,就好像是怪物,[芦毛的怪物]。
视觉的冲击,加上我不知为啥的脑抽,我默认了小栗帽是我理想里骏马所该有的样子,导致那时的涂鸦总是一匹叫小米的灰马。那时候也特地去找了许多资料,也知道了赛马是一项百分之八十看重血统的竞技运动,而小栗帽的出身并不好,早产的地方马,父母皆非名马,出道前只能在北海道的烂泥地里摸爬滚打。如此平凡的出生,最终却进入中央还成为了被誉为平成三杰的著名JRA马,就如同灰姑娘的故事一般的美好。小栗帽的经历感动了那个时代诸多受泡沫经济打击的失落的日本人们,她那传奇的一生甚至能跨越十年触动一个中国孩子的内心。
人总是喜欢赋予其他动物甚至是人造物以人的情感,譬如说对军舰的拟人是由来已久的事了。在我看来赛马大抵也是有一些能与人情感的共鸣。与军舰比,没有宏伟与注定是悲剧的结局,不是那皆恶的战争的附属物。赛马却同有名军舰一样有着傲然的荣耀,那是人类所追求毕生的美好的东西。而小栗帽,那大概是可爱的小小努力家吧。
上初中后摒弃了小时候的诸多不成熟,对马的喜爱也逐渐冷却。人越是长大就越觉得梦想是滑稽且不切实际的讽刺笑话,但人性的复杂既有残酷的成熟,也有继承童年的美好。这恰说明你的心还不甘地反抗着冰冷的生活。被学业与现实压得逐日麻木的我的心里,却永远驰骋着一匹灰马,那是这世上少有的幸运的努力家,大概也是我最原始的梦想。
本故事纯属虚构